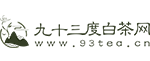- 當前位置
- :
- 九十三度白茶網-福鼎白茶品牌官網-白茶領導品牌
- >
- 茶葉資訊 >
- 正文
- 發布時間:2022-07-23 10:53:26
- 來源:茶葉網
環球快播:安化這盞杯里泡出的山水人文
黃梅時節,也是屬于黑茶時節。
"未至安化縣,先聞黑茶香。"如果說,把黑茶比喻成一棵參天大樹,那它的根就深深地扎在安化。北緯30°是一個奇異的地方。也許是上蒼偏愛,安化就處于這地球南北軸線的黃金分割點附近,奇異當然有的。譬如地球上近九成的冰磧巖就在這里攢山弄水。它獨有的成分,賦予了安化黑茶獨有的魅力。
 (相關資料圖)
(相關資料圖)
黑茶留香,皆因源頭白沙溪。若追"宗"黑茶,我無法溯到一千四百多年前"渠江薄片"的光景,但沿著一些脈絡,比如說從山清水秀的線索,也能尋到入口。
"橋竹碧鮮鮮,岸莎青靡靡。蒼然古磐石,清淺平流水。"安化,不僅是一個能找到前世或來生的地方,還是一卷用資水書寫的黑茶史書。白沙溪,就是這卷史書封面上的印章。
它化身黑白兩種色彩,盡現大氣、穩重之風,彰顯出歷史的悠長。
對白沙溪的浮想生起,我似乎感受出安化山水的美麗,抑或磅礴。
在地圖上,我可以輕易標出安化的經緯度,可到了之后才發現,這是心里的一個地方,打開心扉即可進來。
資水歡唱,楠竹翻波。星羅棋布的村落里,農戶在自家的院落里編織生活。他們仿佛都是技藝精湛的篾匠。白沙溪的千兩茶簍子,大抵出自于他們之手。
雪峰山脈東北端,資水河畔,就是白沙溪茶廠所在了。
一部黑茶簡史,半部安化史。
紅磚青瓦木質屋頂的廠房,頗有上個世紀的蘇聯風格。撲面而來的有四溢茶香,有滿面笑容,還有一份傲視天下的淡定。可那些建筑只是默立,任憑腳步越來越近。
面對許多制茶機械設備,我一時無法選擇從哪里開始。畢竟,隔行如隔山。在這里,我有幸訪到了一位制茶大師。在他如數家珍的解說里,以匠心打造初心,成了公司篤信不疑的信條。
花格蔑簍,聚日月之氣;七星灶里,運轉乾坤。大師說,黑茶制作的工序是嚴謹的,不容有絲毫紊亂。從殺青、初揉、渥堆、復揉、干燥......每一個環節,都是不外傳的秘方或技藝。尤其是"渥堆"發酵以及"松柴明火"的干燥工序。
在白沙溪廠房,有流水線上的黑磚壓制,有張馳有度的手工筑茶,有上千平米的千兩茶曬場……這些都不稀奇,稀奇的是國家二級保護機密的冠突散囊菌培育室。平淡無奇的房間里,蘊含著一個公司睨睥天下的底氣。冠突散囊菌所能做的,除了繁衍就是繁衍。一片片茶葉浴火重生,一定有它乾坤倒懸的法術。
在涅槃成熟的過程中,茶葉會產生一種叫普諾爾的成份,它有良好的防脂肪堆積作用,人們在很早之前就認識到了這個現象。白沙溪黑茶博物館的講解員如是說。
八十年前,彭先澤先生至安化進行壓制黑磚茶的實驗。許多歷史事件被她娓娓道來,顯得舉重若輕,外人聽得卻血脈僨張。
1939年,第一片黑磚茶在白沙溪誕生。
1953年,第一片茯磚茶在白沙溪問世。
1958年,第一片花磚茶在白沙溪發香……
三磚,有黑磚、花磚、茯磚;茶,有天尖、貢尖、生尖;花卷,有萬兩茶、千兩茶、百兩茶、十兩茶。六十多個產品,就是六十多個帶香的音符,一起奏出白沙溪的歷史與尊榮。
那些灰黃衣裳貼身短打扮的杠爺們腳踏乾坤,借用杠桿原理,用力壓制,又再度收緊。一股股陽剛之氣捆緊茶香,使得萬物都靜下來觀看或聆聽。
"壓起來咧!把杠抬啊!重些壓咧!慢些滾啊!大杠壓得好啊!腳板穩住勁啊!小杠絞得勻啊!粗茶壓成粉啊!細茶壓成餅啊!茶香銷西口啊!"一領一和里,雄渾高亢、粗獷古樸。帶有原生態的鄉土氣息流出了梅山千年韻味,道出了梅山人堅韌的個性,說出了山水衍生出的智慧,更展示出幸福來自勞動的鐵律。一種睿智與肉體結合的動作,有了動感,有了力量,有了節奏,它是關于黑茶最美的舞蹈。
偷得浮生半日閑。
如果說黑茶是一出地方戲,那喝茶就是安化人家掛在嘴上的曲調了。這也難怪大明天子相中它,再難割舍。
品是對生活態度和處世哲學的延伸。在白沙溪,需要沏上一盞天尖的。在白沙溪黑茶體驗館,茶藝師為我精心選擇好茶具,整個泡茶流程一絲不茍。純正松煙氣味優雅醇正,飽滿而不艷,在橙黃湯色之上四散。小品一下,滑口生津。
從西邊來的資水像一條舞動群山的水袖。輕輕一甩,就把安化是湖南緊壓茶的發祥地,是全國邊銷茶搖籃的榮耀給抖了出來。茶的香氣里,一口前朝入舊事,一口詩畫出山水,一口光陰似流水。
"茶市斯為最,人煙兩岸稠。"人挑肩扛,車載馬馱,舟楫如鯽,已淡入云煙。那條茶馬古道仍然穿林過巖。資水支流的麻溪河上,竹排還在,麻溪排幫還在,雖然有一絲復古意味,但那些俚歌與放排的號子卻不曾老去。"船艙馬背式"的安化茶馬古道風情,在一杯茶里可以品味出來。僻居一隅的梅山,與萬千山水之外的地方竟然也那么親近。
人生,就是出發,然后休憩,休憩好了接著出發。走出安化,才走出"萬里茶道"的起點。茶馬古道的風雨傳奇,越來越遠。一種勇往直前的精神卻在這方山水里播下了種子。
湯顯祖說,"黑茶一何美,羌馬一何殊。"它牽出黑茶的歷史榮光,卻也道出事物交融的自然規律。看似巧合,實則是自然被時光打磨后的必然。
陶澍說,"尚憶茶始犁,時維六七月。山民歷懸崖,揮汗走蹩薛。"所有的快樂與艱辛,一碗茶可以品出些許味道。多品幾口,幸福卻又那般簡單。
童謠說,"冰磧巖,七星灶,金花朵朵藥;八木春,九重工,雪峰山水沖。"安化人家的日子是從黑茶開始的。從這里蕩漾開去,詩畫實則就是一些至簡的符號和涂抹。
無名氏說,"千兩茶王何曾見,三尖常駐帝王家。"青山綠水,有茶可品,不是神仙一般逍遙,還能是什么?
春也黑茶,秋也黑茶。時間一點一點過去,火氣一點點褪去。
一程白沙溪,盡語黑茶香。
三伏天將至,最為忙碌的是茶人。烘房里的茯茶正在發花。在恰到好處的溫度、濕度中,它正自由呼吸,由著性子重生。
許多根千兩茶被抬至晾曬場,這是歸倉之前的喜悅,也是這個季節最美風景的展示。
山中日月長,鐘愛茶的人,守著青山碧水間的茶園,生死不渝。與茶園廝守,成了他們生命中的一種信仰。
茶催詩興,詩中生茶。歲月如歌,人生過往仿佛是一場穿梭在時光里的故事。從某種意義上說,黑茶已為所有的故事做好了十足的鋪墊。
茶在,一種境界就在。而透過紙背的輪廓,分明是懷舊或回歸的路線。假如豎起一根桅桿,那些長在茶海里的村莊,會不會像船一樣漂著?
從前的孩子已是耄耋老人,萬千風情在他們的敘述中依舊栩栩如生。說來話長,誰又知道會長到哪里。唯有從前的風華絕代,在黑茶的冷暖或縹緲里,或遠或近。
茶來茶去。白沙溪黑茶的烹制,就是人們內心最渴望的味道在醞釀。
行走,固然有一世繁華,停歇又何嘗不是一種睿智?從這里走出的人,心里有兩個糾結,一個是安化山清水秀的誘惑,一個是黑茶刻骨銘心的喜好。在陶澍眼里,出了安化,遇上的就是他鄉故知。可一旦在黑茶飄香前相聚,與誰又都是鄉里鄉親的。
如果說,白沙溪是安化這盞杯里泡出的山水人文,那么散出山水人文的,就是那些情意濃濃的黑茶吧。